《战争与和平》中,托尔斯泰笔下的19世纪沙俄贵族们乐于用法语表达自己的思想,尤其在涉及严肃的政治题材或哲学思辨时,仿佛用俄语便不能阐释清楚,于是非得说法语不可。而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描绘的法国上流社会又以使用拉丁语为荣,特别在论述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时,似乎只有拉丁语才是与神沟通的语言。
那么使用拉丁语的人呢?作为希腊文化的继承者,罗马人毫无疑问要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字母中汲取营养……
西方人对语言的态度不仅使我联想到国人对英语的爱恨交织。在我看来,对母语宗教狂热似的崇拜,不是一个开化的民族应有的表现。使用母语的同时,尊重、学习并使用另一个文明的语言,也绝非“不爱国”或者“文化叛徒”。倒是一辈子守着母语不放、不能阅读原版的国外作品、不能与外国人用其他语言自由沟通的人,才是文化鸿沟的奴隶。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
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的距离。而是我站在你面前,你不知道我爱你。”
一周前我还像许多人一样,以为这首诗的作者是泰戈尔。而且我比许多人更愚昧的是,从前在广播里听DJ读到此诗,而且说明作者是张小娴时,自己做出了两个无良的判断:一,张小娴引泰翁诗不注明出处,属于人品问题;二,DJ胡征乱引,盲目崇拜(而且崇拜错了人),属于智商问题。
可是后来机缘巧合,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《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》一诗前世今生的详细文字,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人品和智商都有问题……
事件有点复杂,简而言之,目前比较流行的《世》有三种版本。版本一就是前文引用的,张小娴在小说《荷包里的单人床》中创作的初版(与小说中稍有改动),这个版本流传最广。版本二有四段,将张小娴的原版作为开头,以接龙的方式叙述下去,最后一句是“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得人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”——传说此版是台湾一群医科大学的学生在BBS上集体创作的(所以才形成了接龙的形式)。版本三应该是林夕的手笔(对于这首诗各版的出处,措辞千万要小心谨慎),也是我最喜爱的版本,它的前半部分以接龙的第二版为蓝本,后半部分以物喻人,同样采用接龙的方式,最后一段是:
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是鱼与飞鸟的距离。一个在天,一个却深潜海底。”
那么,此诗的原创是泰戈尔、出自《飞鸟集》的说法又从何谈起呢?大概是因为某无名氏把第二版翻译成了英文——翻译得比中文版毫不逊色——造成了不知情者以为原诗可能是英译中的猜测,加之他们感觉本诗的风格与泰翁诗有些相像*,于是作者阴差阳错变成了泰翁;至于为什么出自《飞鸟集》,显然是林夕版的最后一段让人产生了误会。最后,《读者》杂志又不负责任地将本诗引登在03年14期上,署名“泰戈尔”,(引用自何处说来话长,但因为《读者》的影响力而将其视为“罪魁”,当无疑问)——于是“谎话被人说了一万遍就成真的了”……
* 虽然自己没有通读过《飞鸟集》,但就读过的一些泰翁诗来看,泰翁一向含蓄而温情,很少如此直接地抒发男女之爱,“世界上最……”这样的开头也略显浮躁,不是泰翁的风格。
个人觉得这个“三人成虎”的故事非常有趣,至少透过它可以引发许多思考,这里就不发散了。不过,既然能让无数人心甘情愿的把《世》冠名给泰翁,至少说明它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水准(不相信的人可以试着自己捏造一首,看看有没有人会上当,能有多少人上当)。
“但网上一位学者评价,将这首诗放在任何一位抒情诗集中它都不会逊色。这首诗将暗恋中男女的绝望层层抽剥,直至最不可触摸的隐秘末梢。那种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幸福,就因为没伸手而永世错过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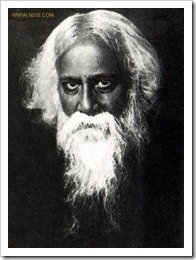
拉丁语曾经是西方上层社会的主流貌似是因为它严格的语法,英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.
阅读原版的国外作品才能更好理解作者的本意,他/她到底要表达什么.不得不承认语言是门很奇妙的学问.翻译过的著作有时候会误导读者.泰戈尔的诗集不错,可惜只看过中文译本.
原来…之前看过一个版本是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…还以为是泰戈尔原作…………//